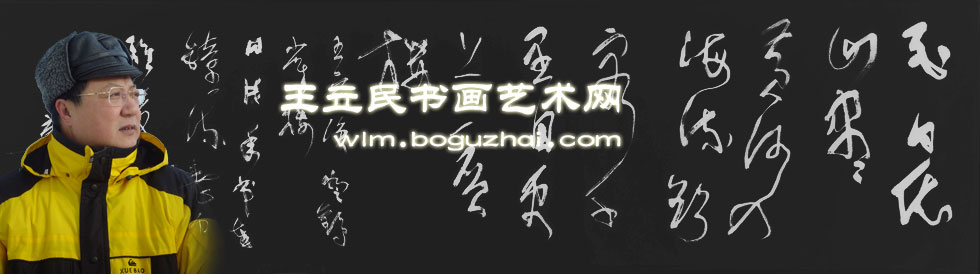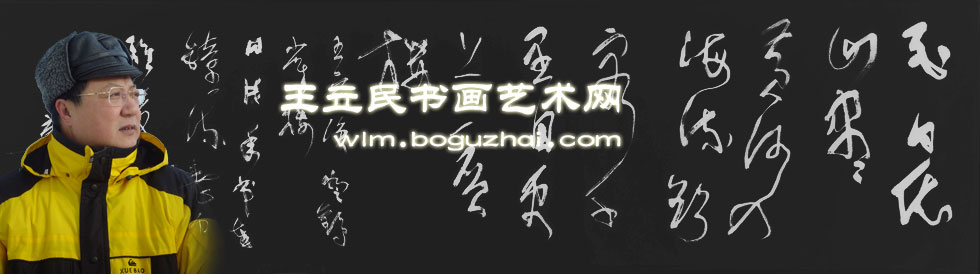“集形短句”是汉字形成发展中由萌芽期到成熟之间的重要形态
王立民 著
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。《周易·系辞》中说,文字起源于八卦,是由庖牺氏创造的:“古者疱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,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这种神话传说虽然未必可信,却为中国文字起源于“象形”这一点提供了启示。
还有一种说法,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“结绳”。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叙中说:“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。”结绳是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用以帮助记事的一种方法,结的大小、多少和位置的不同,都有不同的意义。但,结绳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备忘的记号,它只能表示事物的“存在”和“否定”。不含有任何叙述性和实际内涵,当这个事物不存在或完成时,它完全失去意义。因而正如高明 先生所说:“它既没有社会意义,也不能担任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。彼此具备的条件不同,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同。因此,结绳不等于文字,也不能发展成文字。”
到了战国时期,社会上流行一种“仓颉造字”说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中说:“故好书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者,一也。”荀卿的看法是有道理的,在众多的“好书者”中,仓颉应是最优秀的,他之所以“独传”,是他总结了文字创造的规律而传之后代,可见,仓颉对文字的产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仓颉是一个人?还是一群人?我看以后者为确,因为文字的产生决不是一个人的事,一定是掌握书写权力的一个阶层人的努力,或者说仓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。
以上的传说说明一点,即中国文字的产生,主要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物。中国的原始文字,可以说是远古社会生活图景的浓缩和写照。但我们认为,中国文字的起源一定很早,这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交往的增加所决定的。因为,第一,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新时代时期的玉器看,当时人类的大脑已经相当发达,从玉器制作的对称性、相等性、方圆关系、凸凹表现看,人类的劳动技术已非常精密,审美观已相当高。使用这样精美的玉器,说明人类交际已达到了相当频繁的程度。有这样思维和审美意识的人类,应当产生文字。第二,由于人类文明的多元化,语言的多元化,文字必定是多元的,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汉字只是其中的一种,其它文字在我国境内逐步被汉字替代而消失。
一、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
文字产生于人的交往、生产劳动和审美意识的外化。是出自人们迫不得已的需要。早在原始社会晚期,汉字产生之前,人们为了记事和抒发自己的情感,在生产生活工具上刻画下了一些符号和图形。陕西西安半坡、临潼姜寨、 合阳莘野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;甘肃半山和青海马厂、青海乐都等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;山东章丘城子崖、青岛赵村等地龙山文化遗址;浙江良渚,江苏上海马桥、青浦崧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,均发现刻划在陶器上的形状相似的符号和一些图形。
说这些符号是汉字的萌芽,是因为,一标识性。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,它包括甘肃临洮马家窑、兰州青岗岔、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20多处重要遗址。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。这些彩陶就是今天看,也已是相当精美的艺术品(加图),由于当时大规模进行陶器生产,必定存在陶工和画工的相对专业化,这些相对独立的人员在制作自己的陶器时要有自己的标识。1974年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墓葬中,发现在殉葬陶壶的腹部或底部有涂画的符号,而且每件器物只画一个,共有50种(图中国古文字通论P34表四)。有的符号相当接近或相同,如∨ㄥ∧ 等,每一类可能是一个陶工或者一个生产小组的标识,就象今天陶器底部的印记代表着一个人或一个厂家一样,它的标识性已非常明显。二,顺序性。顺序性即数字概念。古代先民在非常早的时代就有了“数”的概念,比如传统中的结绳记事,就是一种体现。在马家窑文化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带缺口的骨片,在柳湾的一个墓中就发现49片,每片各刻1个、3个或5个缺口不等,这是一种记数的工具。同样,在西安半坡村原始公社遗址、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姜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中,有很多简单的,类似于今天数字的符号。于省吾先生曾认为其中的×、+、 即是数字的五、七、十、二十。这种数字的概念是文字内涵中的重要内容,代表着古人类的思维已进化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。三,述事性。文字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。它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,在于叙述一件事或一个物体。于省吾先生把这些符号中的 解释成示、玉、柔、 、阜等。我以为其中 可释作齿、 可释作大、 可释作足、 可释作天, 可释作丝、 可释作日、 可释作目、 可释作品、 可释作手、 可释作中、 可释作云。其中 、 等可释作先民的一种生殖崇拜意识。马家窑上的孙家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(图同前始祖118),五个女子携手而舞,与甲骨文中的 字几无所差,只不过舞蹈纹彩陶盆上的手手相连,而甲骨中表现的是手执兽尾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鸟纹钵(图始祖84),同金文中的象形字同出一辙。象这样的例子很多。它具备的比较完整的述事性,证明了文字在萌芽状态所具有的功能。在考古研究和古文字研究中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就是古人在当时时空中,是相当聪明的。这一点我们从大量出土的玉器、陶器、铜器中可以印证。所以不能过多的疑古。在文字产生以前,古人用陶文符号和图形留下的思想意识,一定是相当丰富的。
陶文符号和图形所具有的标识性、数字概念和述事性,已经具有文字的基本功能,但是这种功能是简单的幼稚的,还不能连续表达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,所以它是一种文字的早期的萌芽。
陶文符号和图形的发展有两条轨迹,一是逐渐发展成文字;一是继续发挥它的简单标识和装饰作用。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的陶文符号,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的陶符,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及战国时期的陶符,以至今天陶器上的印记和图形。但它否定不了第一条轨迹的发展,就象猿类,一些进化成人类,一些仍然是猿一样,两者有质的区分,不能混淆。
二、金文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是汉字的初始期
汉字由陶文符号和图形发展到成熟的文字——甲骨、金文,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目前,我们还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字,但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看,我们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、图形与甲骨、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金文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相同的形态。
金文族徽,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它。我在这里讲的“集形短句”应是这样的概念:它是由几个象形文字组成的、不能构成词组,但能完整地反映一个事件过程的短句。为什么叫“集形短句”而不叫“集字短句”呢?因为这个短句,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字的构成,而是完全用“形”来描绘这个事件。“集形短句”在金文中被广泛应用,说明它是在甲骨、金文的前一个形态中被长期使用、约定俗成的一种形态。而在后一种文字形态中被保留了下来。
比如,祭祀是上古先民一种最重要的活动,凡国家、部落皆有祭祀。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主要是祭祀上天、神灵和祖先及已故的部落、国家首领。一是以人作祭品,另一是用人扮成神灵。在金文中有如图 ,曾被多种金文中重复使用,这是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小孩坐在“几”上扮作神灵进行祭祀的形式,因为这种形式是固定的,所以它的记述方法也被沿用下来。另如图 ,和图 ,前者说明被祭祀者生前曾从事渔业生产,后者说明被祭祀者生前是畜牧业部落的领袖。
在文字表情达意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,这种“集形短句”自然是非常便捷而实用的。就是在甲骨金文时代,“集形短句”被广泛使用,应是一种对事件的“缩写”,就象今天使用成语一样。
族徽与“集形短句”具有同样的意义。族徽是部落氏族的一个固定的标志,它的生产应在国家产生以前。它是比“集形短句”更早的带有述事性的符号。商代早期青铜器上没有文字大概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,可一但能够铸文,首先铸上带有标志性的族徽。由此可见族徽的产生早于甲骨文和青铜文字。
胡小石先生把中国文字的发展划为三期,第一为纯图画期;二为图画佐文字期;第三为纯文字期。而前两期的图画中族徽为重要内容。唐兰先生在《古文字学导论》中提出“文字的起源是图画”,是合理的。这里的图画应是包括陶文图形、金文图形和族徽。而族徽的述事性又比图形更接近于文字而包涵的内容更加丰富。游寿先生认为“初期青铜铭文:最早族徽,稍后有祖父和干支字。到‘作’字,动词出现能记事” 。族徽与“集形短句”比,更具有以下的特点:第一,标志性更加明确。族徽为一个部落的最重要特征的代表物件,是一个部落的象征,比如一个部落曾经猎获过大象,这成为这个部族最重要的事件而引起部族成员的骄傲和自豪,这个部落就以获象为标志。(如图游P1.最初)房屋成为最具权威的人才能享受的“高级奢侈品”,人们把房屋视为最神圣的事物,所以以房屋作为自己部落的标志(如图金文编1094)。第二,理想性更加丰富。上古人类由于对自然事物的认识的程度有限,所以对很多自然现象产生一种神秘感,比如雷、电、风、洪水等等。即畏惧又崇拜,所以有很多以神秘事物及古人的想像为自己部落的标志,以展示一种威严和神秘,如以龙、凤、蛇(金文编P1087)及类似后来“符”的一些人兽结合、张牙舞爪的神秘图形(如图金文编P1085)。第三,述事性更加复杂。“集形短句”是由几个带音的图形(后来成为文字)构成一个完整的、固定的事物,而族徽是由一个或组合的图形来完成更加丰富,更加复杂,更重要的一个事件或意义,有时是一种精神或意志的概括或提升。如图(金文编P1054)“外 形象宗庙, 中一妇首戴胜而奉尊。妇可主祭也” 。妇女主持祭祀,这是母系社会的风气,此图形在很多金文中出现,证明它是流传很广、很久又被人们广泛承认的共同标志。很可能是上古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留传下来的,后来又被这个氏族部落各分支所使用的共同的标志。这种使用如此 广泛的标志,被认同的广泛性说明它一定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或传说。
由陶文符号、图形到金文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,这个过程代表着人类记录和传达语言、事物能力不断增强,它的根本动力是人们交往的扩大,使得人们有一种非表达不可的欲望,它表明人类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、由蒙昧走文明的历程。
三、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
中国汉字经过陶文符号和图形到金文族徽和“集形短句”,逐渐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文字,即殷商时代的金文及甲骨文。
殷代金文及甲骨文为汉字成熟期的标志,即可以从它们中间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,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也符合这些规律。这个规律即“六书”。
“六书”是汉字理论研究一种古老的方法。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,仅靠六书是不能完全解释了的。但六书作为汉字研究的基本规律,曾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这充分说明了六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。故而,以此作为汉字成熟的标志是应当成立的。
我们认识六书,应当是这个顺序,六书是从汉字产生中总结出来的规律,又指导汉字的发展。汉字在先,六书在后。千万不可反之。
“六书”字样,最早见之《周礼》,东汉时班固、郑玄和许慎,此三人中,以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最为著名,影响也最大。目前,我们已经发现了战国时竹简的《说文解字》,所以说《说文解字》已不是我国的第一部字典了。但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在研究文字发展的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,是不容质疑的。许慎对六书的排列次序为: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。而班固与郑玄的排列顺序与之不同,自宋以来,研究六书者也各抒己见。根据各家研究成果的不同,笔者认为其顺序应为如下: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假借、转注、形声。
一、象形。许慎说:“象形者,画成其物,随体诘诎,日月是也。”即用最简练的图形,描绘其事物的形体。这种图形逐渐成为一种符号,即象形文字。二、指事。许慎说:“指事者,视而可识,察而可见,上下是也。”指事是一种以象形字为基础,增加其抽象符号,以指出某一事物的特质。三、会意。许慎说:“会意者,比类合谊,以见指 ,武信是也。”会意字是把两个(或两个以上)象形字合为一个新字,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。四、假借。许慎说:“假借者,本无其字,依声 事,令长是也。”即“借”已有的字来表示新的意义。由此而开汉字多音多义字之先河。五、转注。许慎说:“转注者,建类一首,同意相受,考老是也。”“转注”为相同意义的部首,加上不同的笔画,但又可以相互注释的训诂方法。六、形声。许慎说:“以事为名,取譬相成。江河是也。”形声是一种用表意、表音两种固定符号组合而成表示一种新概念的造字方式。
以上对“六书”的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,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属于造字的方法,转注是一种训诂的方法,假借是一种用字之法。
而我们研究“六书”,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。第一,“六书”在造字和用字的过程中被总结出来并进一步促进文字的发展,这是汉字成熟的一个标志。即殷代金文及甲骨文是具备“六书”规范的文字,所以它们是汉字的成熟期。第二,学习书法,应当对“六书”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。首先,了解“六书”对于掌握汉字的发展史是一个根本的基石。其次,学习书法,尤其是学习篆书和篆刻,不懂六书,是难成大器的。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大家,尤其是有清一代的书家,都对六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,由此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。
六书在文字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断代特质,以六书为尺度,衡量殷商时代的金文和甲骨文,完全可证明这个时代文字已处于成熟期。至于隶书以后的汉字,因转为另一种符号形态,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内。
在文字发展过程中,陶文符号、图形和殷商金文、甲骨文被很多专家学者所熟见和深入地研究,这是文字萌芽期和成熟期的明显标志和形态。在两者的过渡段中,族徽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形态,本文提出“集形短句”的概念,其实“集形短句”在金文中的存在已相当普遍,但是作为文字萌芽期到成熟期中间的初始期的形态,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。
2001年正月松花江南岸三宜阁
高明《中国古文字学通论》P31页
游寿《历代书法选》P1
胡小石《书艺略论》P207
|